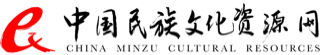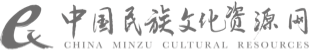吊脚楼的现实与神话

吊脚楼是贵州黔东南苗族、侗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,与苗族、侗族本身的历史一样,吊脚楼也有很多神乎其神的传说。
在锦屏县西部的平秋侗乡,祖祖辈辈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吊脚楼的故事。说是某木匠师傅因跟友人打赌,一夜之间竟然建完一栋三层三间的吊脚楼。传说的真假而今已无从考证,能够一夜建成吊脚楼的木匠师傅到底姓甚名谁、何方人氏,连我身为木匠的爷爷也说不清了。
童年的印象中,我这个侗家的孩子也不知道侗家人的房子是如何建起来的,只依稀记得每逢村里有人建新房,大人们必先出去忙活一夜,第二天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总能看到一栋崭新的吊脚楼拔地而起。带着对木匠师傅的神往,我在离开家乡若干年后,又回到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。这一次我被允许参加吊脚楼建设的全过程,童年的那一丝疑惑在这一刻终于豁然开朗。
那是2008年的冬天,百年不遇的冰冻雨雪灾害席卷黔东大地。姨娘家因灾无房须重建一座吊脚楼,我是家里的成年男丁,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义务建房的队列。
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气温骤降到0℃以下,鹅毛般的大雪倾刻间便没过了鞋帮。这样的一个夜晚,要去户外完成建房这样一个艰巨任务,方登弱冠之年的我心里面只有两个字——惨了!
晚上23时刚过,正准备进入梦乡的我被姨父从床上叫醒,我迷糊着双眼跌跌撞撞地奔向工地。工地上没有灯,大概是因雪灾影响而停电了。村里的老少爷们正围着三五堆篝火有说有笑,他们在等角落里一盏煤油灯下的“大师傅”结束那没完没了的“嘀咕”。望着一张张朴实、憨厚的熟悉面孔,我迅速融入了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义务工程队。
零点左右,随着主人家的一通炮仗,“大师傅”的“嘀咕”终于停了,他宣布当天的中心任务正式开始。围在火堆旁的人群开始骚动,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争先恐后地爬上预先搭好的支架,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则奔向旁边一堆堆预制好的木结构部件。
没有人分工,一切都约定俗成。“大师傅”在一旁挥着尺子喊话,先装什么,后装什么,谁拿什么,谁扛什么。几十号人的队伍,没一个人歇着,也没一处乱着,一幅生动的劳动场景,顷刻之间就已经铺展开来。初次身临这样复杂的劳动场面,我一时竟不知从哪里着手。“大师傅”一看,笑了:“小伙子,你就递递锤头添添火,先学着吧!”“这活儿倒简单!”我“扑哧”一乐,一时竟忘了自己是以成年男丁的身份参与进来的。
一根根木结构部件被拼接起来,先以“组”编装,再以“厦”拼立,最后以“间”对接。中年人在地上奔忙着,青年人则在房梁上跳跃着,一时间吆喝声、口号声、敲击声响成一片。
在火光的映照下,雪花飘得更密、更白、更那么寒意逼人。在众人的踩踏下,积雪化作污浊的泥水。地上,我烤着火,浑身却冻得瑟瑟发抖;10米高的房梁上,乡亲们一边说笑着,一边甩开膀子敲榫头。除了我,没有一个人感叹这雪下得那么气势汹汹,那么如梦如幻。一层,两层,三层,房子的高度逐步显现;一间,两间,三间,楼房的模样渐渐成型。
“等一下!”就在三间木房的拼装工程即将结束的时候,“大师傅”的一声断喝让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了下来。原来那最后一个部件的榫头,“大师傅”忙中出错——做反了。
姨父好像早有准备,迅速将一根半成品递到“大师傅”手里。“大师傅”则轻车熟路,不到十分钟,一个新部件就迅速成型并装上了房梁。“不错……不发……错发……错发……错了就大发……”在“大师傅”的唱祝声中,叫好声、鼓掌声、敲击声再次响成一片,姨父的脸上也露出了舒心的笑容。
失误了还能微笑?我心里疑惑起来。后来回家问爷爷才得知,原来侗家人装房子是有讲究的,最忌的是精准无误、分毫不差,所以一般木匠师傅都要有意无意地造成一些小“失误”,以便因势利导地给主人家带来祝福。
天麻麻亮的时候,主人家的女眷送食物来慰问了。当表姐将一碗热腾腾的油茶递到我手上的时候,我才从如梦如幻的劳动场景中惊醒。
百余个形态各异的部件,二三十个没有技术的乡亲,就那么六七个小时,一座吊脚楼却已从无到有悄然耸立。那个木匠师傅一夜建房的神话,这时候离我是那么近,那么触手可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