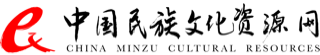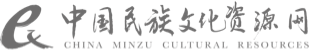阿舍三个短篇的维度
1
阿舍的散文读过,喜欢。阿舍的小说第一次读,总体上感觉,是达到了一个长期自觉地进行着艰苦的文学训练的作家应有的水准。这组短篇,用于《西湖》的“新锐”栏目,那么,是不是可以这样说:有着这样一群质量整齐的“新锐”,我们的文学就是有理由乐观的了。有趣的是,不知道阿舍是有意为之,还是无意使然,这三个短篇恰好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维度,于是尘世与天堂次第呈现,为我们说明了小说做为一门艺术可能会抵达的高度,和容易跌落的陷阱。
2
《苦秋》站在尘世中,因此难免遵循了尘世的一些重要属性——非此即彼,一览无余,逻辑坚硬,因果昭然。在《苦秋》里,与贫穷相伴着疾病,与疾病对应着生理意义上的救赎,即使偶有精神层面的漫漶,也不免流于漫不经心。是的,它很“实”,实到在一个短篇的容量里有些略为笨拙了。就是说,这样的一种煎熬,对于活在尘世中的我们已经司空见惯,更严厉一些的说,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简单重温。好在,这个短篇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“陌生感”,奇特的人名,宗教色彩,尽管没有着力渲染,那种“异质”的力量已经部分地承担起了一个短篇小说所应达到的效果。奇妙的是,这种“异质”却弥散在了整体的“庸常”之中,不由分说的艰难导致出可被推理的灾难,从而灾难也成为了必然,就像小说的题目一样,《苦秋》,这个太过熟稔的意象,使一切归于不出所料的结局。小说的结尾恰是如此——“马尔焉终于如愿以偿”。那么,阿舍是否在这个短篇中“如愿以偿”了呢?我想阿舍没有令自己安心,否则,她不会在一个一万字左右的篇幅中,弄出以胎为药的事情来。窃以为,小说最后一段可以略去,在“过来,你抱住我”戛然而止。当阿舍强调马尔焉的如愿以偿时,是否已经透露出了她做为一个小说家的心有不甘?当然,这种揣摩和猜测,不应当强加给读者。
3
《奔跑的骨头》介于尘世与天堂之间,她并不满足在尘埃中辗转,向下,她甚至掘地三尺,弄到了矿井,弄到了坟下,向上,她舒展到要用兔子的尸体来测定灵魂的重量。做为一个短篇,她有根有据,有理有节,在满足了现实逻辑的同时,又努力向上升腾,去捕捉那种“不可言说”的小说逻辑。于是,尘世的逻辑不再是那么坚硬了,世界变得模棱两可。有一个人不知所终,隐匿在时光的背面,激发出妻子“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”的执拗,然而,当一切都皆有可能时,这种执拗也变得不那么一根筋了——“映照爸如果突然回来,会比死了更让你害怕和伤心”。喏,小说散发出了她迷人的光芒,内容和形式都因此而结合得堪称完美,她贯彻了自己这门艺术的一项基本规矩,那就是:小说不是要描摹“是什么”,而是要提供出“可能会是什么”。当这项规矩得到了忠实的贯彻,小说不奔跑都不可能——“那些白哗哗的骨头没命地跑”,而做为读者的我,必定被她带动着“拨腿就追”。好的小说,就是应当让读者不遗余力地去追赶吧?阿舍在这个短篇中展示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专业水准,有天赋,有技术,不动声色,却意韵无限。
4
《核桃里的歌声》宛如在天堂吟唱。我毫不讳言自己对这个短篇的喜爱。尽管,从某种短篇小说的“行业标准”来说,她的确是略显单薄了些,但唯其如此,才使得她具备了一种轻盈之美。而且,我甚至要这样判断,这个短篇的气质,也恰好是和阿舍本人相一致的。相对于“大声疾呼”,阿舍也许更适合这样的“轻声呢喃”:把你的手儿拿开,放在你的心上,那里是我,最秘密的故乡。当阿舍在《奔跑的骨头》中证明了自己做为一个小说家的能力后,终究还是要向着她“最秘密的故乡”飞翔。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?显然,那里有悖于“青山人的幸福”,“那儿的人看似不幸”,“那儿的人四处寻找歌声”,那儿的魅力,宛如一个“皮肤滚烫,肌肉很结实”的男子对于怀春少女的吸引力……不是吗?很虚无,很颟顸,然而,却很曼妙。阿舍在这个短篇里,营造出的那种普世的景致,庭院,舞会,丰韵的母亲,乃至抽象意义上的“青山”,即使上下浮动几百年,都是人类能够普遍体察的,这种高度寓言化了单纯和透彻,似乎更切近文学的内核。最为可贵的是,阿舍在这个短篇中,坦言了 “羞涩”——一种不属于“青山人”的情怀,而这种面对尘世时,如影随形的“羞愧难当”,对于一个小说家,是多么重要的一种品质。
5
是我人为地将阿舍的这三个短篇划分了疆界,并且,自以为是地确认,阿舍更加适合最高处的那种表达吗?我的依据是:三个短篇,尽管气质各异,但在叙述上,阿舍总是不能避免地发出自己最娴熟的那种声音,怎么说呢?嗯,有些不可遏制的抒情愿望,这是阿舍得心应手的,但在处理《苦秋》这样的题材时,不免就有些 “文艺腔”的弊病了——“马尔焉想,今后我的世界,难道必须承受和允许这种缺失么?”相反,在《核桃里的歌声》中,这种文字反而却显得落落大方——“白天它们忙着咀嚼阳光,沸沸腾腾无暇顾及我。”就是说,阿舍替“我”说话时,是驾轻就熟的,但在替马尔焉说话时,就稍嫌力有不逮了。当然,这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,何况,抒情之于文学,总是没有大错的。
6
还有一个依据:阿舍不是一个能狠下心的小说家。她让马尔焉“如愿以偿”,让映照妈“放心地骑车回了”,这些结局的根源在于,她让歌声缓缓升起,时光一般刊刻在那个“我”的身体上。这样的一种姿态,和煦,安然,不是更适合在高处飞翔吗?也恰是如此,尽管内心激烈,阿舍小说的结局却都会无限敞开,让一切不堪都归于朴素,这对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种杀戮般的结尾,那种炫技般的,过度的“重重一击”,不啻于一种必要的纠正与温和的平衡。
7
三个短篇,还有一个有趣之处:篇幅相差居然只在百字左右。如此均匀,阿舍是掐着指头写出来的吗?《苦秋》差不多,多写无益,少写大约也不足以成为一篇小说;《奔跑的骨头》是不是该稍微长一些呢?称兔子以测灵魂,多好玩啊,我没看够;《核桃里的歌声》也许洗练些就更好吧?毕竟,来自天堂的声音是那么稀有。
8
无论如何,阿舍以她不同维度的述说,为小说的魅力做出了证明的同时,也向我展示了她做为一个小说家前行时的诸多可能性,恰是这种可能性的丰富和立体,使得阿舍的小说值得期待。